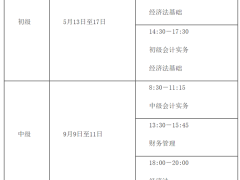去了長沙和廣州兩地,回來以后才真切體會到,嘿,這倆地方的人咋就差別那么大呢?先說說最近的這趟旅程吧,啊哈,說實話,挺讓我開了眼界。
講個最直白的,長沙和廣州這倆城,氣質完全不是一回事,南方人也不是你想象中那樣,都熱情得一樣。出門前,我還跟朋友吹牛:“南邊人不都差不多,去哪兒都能當朋友嘛。”現在回頭看看,哎呦,還真是自以為是了!
說說最后一站先,廣州那個地方,來了才知道,人家確實淡定。下了高鐵,一進地鐵站,大家人來人往卻都挺安靜,沒人吵吵嚷嚷,問路的時候,碰到的是個慢吞吞的大叔,話說得特別溫和,指路動作都不急,整個人散發著一種“沒事兒,慢慢走”的感覺。和長沙比起來,誰敢說廣州不“溫吞”啊?
再說啊,廣州街上的早茶店,那氛圍更是靜悄悄的。那些坐一桌的老人家,喝茶咬鳳爪,聲音低得幾乎能聽見茶葉泡開的聲音。我點了蝦餃,旁邊阿姨用帶口音的粵語提醒我加個腸粉,聽著別提多舒服了。廣州人的熱情,就是這樣慢慢滲出來的,沒啥轟轟烈烈,但讓人覺得踏實。
再逛逛上下九步行街,越秀公園,沙面那些地方,人來人往卻不吵鬧,大家好像各忙各的事,根本不打擾別人。廣州人待人很有分寸,消費上更講究精打細算,看那買單的架勢,絕對不是隨便花錢,雖然錢多,卻從不張揚。
晚上廣州的夜宵攤也別有一番味道,煲仔飯、牛雜、甜湯,清清淡淡的,溫溫潤潤的,吃完一鍋靚湯,渾身像是被舒展開了似的。我還跟當地朋友聊美食,基本無一不是圍繞著哪里有地道好吃的,哪里性價比高。他們說話輕聲細語,見面點個頭就算朋友,真要說熱情,也是細水長流那種,不像長沙的火爆。
廣州這邊司機師傅開車一般都不說話,專心致志,我搭話兩句人家也就“嗯嗯”應付過去,真是留三分的風范。你看那美食鋪子老板,招呼客人特平淡,沒人硬拉你進去,消費者自己挑,像個安靜的下午茶時光,有點江南的味兒。
不過呢,換個地方,回頭說說長沙。剛下高鐵,撲面而來的不僅是熱浪,更多的是濃濃的煙火氣和人氣。哎呀,那種感覺就像突然被一鍋沸騰的辣鍋裹挾住了,炸裂得不得了。
長沙人講起話來大嗓門,熱勁十足,你問路,那小哥立馬給你畫活地圖,就像是非得把你拎到目的地不可,勁頭十足。剛出地鐵站,就看到奶茶店門口一幫小姐姐自顧自拍,笑得甜蜜得像喝了好多甜酒。五一廣場、黃興路、坡子街這些地兒,隨便一條街都是人山人海。
長沙人見了陌生人熱情得好像過年似的,“來長沙啦?臭豆腐吃過沒?”“跟我來,我帶你去!”這話絕不是敷衍,我跟隨他們走進一條深巷的小攤,老板娘一邊燙臭豆腐一邊問“吃辣不?”我硬著頭皮說能吃,結果嚇得嘴巴冒煙,長沙小哥在旁邊一頓樂,笑得拍桌子。“長沙人辣嘴子,心腸熱。”
天黑了,解放西那邊簡直是個大聚會的現場。酒吧門口跳動的人群,奶茶旁邊的燒烤攤,烤串的香味混合音樂聲,空氣里全是躁動。長沙人說話帶勁兒,久了你就覺得挺親切的。
打車碰上的司機師傅更有意思,說起這兒的夜生活那眼睛都亮了,“長沙晚上不睡覺,白天醒不過來。”凌晨兩點的街頭依舊熱鬧著,跟剛過節似的。我還試著跟著當地人喝了酒,一杯下去頭暈腦脹,朋友戲謔一句:“你還真不行”,差點噴酒出來。
長沙的夜晚不愿裝模作樣,就是那么直接,那種熱情蔓延到每個角落。大排檔老板、奶茶小哥、咖啡店貓咪,路邊小孩,不管誰都愛搭話,冷場這事兒最怕了,話題不停地蹦出來。沒準一不小心被拉進麻將桌,輸了錢還得聽笑話“手氣太差”。
長沙人有時候真的“社交牛逼癥”,跟他們混一塊兒,連想獨處都難,畢竟人家最怕冷場,要不就是“爆炸現場”。那種熱情,有些時候會讓人覺得招架不了,但又覺得暖洋洋的。
到長沙吃東西同樣有苦惱,小吃攤排長龍成了常態。臭豆腐、糖油粑粑、螺螄粉,老板手都快抽筋了,根本招呼不過來。有次我等得實在不耐煩,前面的年輕人居然說:“哥,別等了,估計排到明天去了。”我信了,結果半小時后來聞著香味,差點沖進廚房搶鍋鏟。
整個長沙就是這么一鍋火辣辣的生活,風格鮮明,灑脫得很。當地人說什么“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天的事兒明天再說”,活脫脫一副生活哲學。
走的時候,我還順手學了幾句湖南話,“不得行”成了我的口頭禪,跟路邊大媽聊上幾句,跟小攤販講講價,整個人像是被這座城的“社牛精神”附體了。
你說這倆地方,長沙和廣州,真就像是火鍋跟湯一樣,一個辣得夠勁兒,一個溫潤如水,各有各的味兒。南方城市沒那么容易一刀切,兩個城市活生生把南方人的性格演繹成了兩個極端,熱辣與溫和,張揚與內斂。
說到底,長沙教我的,是怎樣放開膽子熱鬧;廣州則讓我學會了慢下來,靜靜享受。只不過,這份體驗也就只能現場感受了,別人說破嘴皮,也說不清楚。